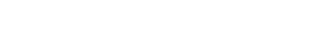关键字: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玉海 李佩珊 3月13日下午,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咖啡厅见到刘守英教授时,他说,他前两天刚从老家湖北洪湖市的村里回来。
这次采访他,是想请教乡村振兴的问题。在中国完成脱贫攻艰之后,乡村振兴是有关农村的最新顶层设计、国家战略。而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30多年的涉农研究、调查,使他成为当前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权威,且有着切身的乡村经历与关怀。
刘守英教授从他最近的这次回村见闻讲起:他看到了乡村今非昔比的巨变,也看到了日渐富裕的乡村外表掩盖之下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农民辛苦多年形成的资本积累几乎都变成了闲置在农村的住房、大量耕地被占用、奋斗在城市的农民归属不定而这一切问题,源于中国上一轮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
在他看来,从“70后”这一代开始,改革这种以农民工最终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他说,“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就难免变成下指标、乱作为;如果乡村振兴弄成赶人上楼、再把地腾出来给城市做建设用地指标,那没有意义的。”
以下是刘守英教授的讲述:
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
从十九大开始,决策层意识到,乡村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好事。
在十九大之前,尽管一直在说“三农”问题,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讲农业怎么保证供给,另外就是农民怎么增收。农业保供给,实际就是粮食增产的问题,还是从乡村怎么为国家保证粮食安全这个角度看问题;讨论农民增收,比讨论纯农业问题往前走了一步,农民得有收入,但解决农民收入的方式不只是在农村。
后来证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是靠农业,主要还是靠农民出去、在农村以外找到收入。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乡村令人担忧之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第五个问题:坟地越来越奢华。
家族跟家族之间,相互不光是比房子,还比墓群、比坟地规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乡村有很多陋习。
一定要强调:乡村一定要禁止占用耕地盖房、建坟墓,未来一定不能以原村落的地址做家族墓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出来。尽管有人会骂我,但也得提。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墓地的占用。
城市化的低成本由乡村在承受
我们把这些图景拼起来,结论是什么?整个中国上一轮城市化模式的代价,都是由乡村在承受。这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问题。
很多人讲,中国的城市化——让农民年轻的时候进城打工,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是因为各种保障低、福利低。农民在城里做了贡献,但他应享受的福利没有得到。城市政府低成本,是因为本该由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支付的成本没有支付,包括这些人的居住、孩子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品。
中国城市化的所有这些低成本,都是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农民在城市还是农民,被叫做农民工,只是一个在城市作为农民身份的工人,城市所有相关的公共服务、市民的基本权利,都跟他没有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的那套工业化体系,靠的是农产品的剪刀差、统购统销,来保证城市低工资、低食品价格、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后这一轮工业化,实际上是靠城市少支付进城农民的城市化成本,快速城市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这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建立在不支付农民城市化的成本、不支持人进城的城市化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总是有人来支付的,是乡村在支付。整个乡村的代价,是由这套城市化模式带来的。
为什么中国在城市化率才只有60%的时候,要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因为:乡村的凋敝、农村老人的绝望、农民的归属不定,孩子没有未来,农业没办法发生要素重组的革命,大量的资本积累在乡村导致资本的浪费
这样,乡村就变成一个“愁”的地方,而不是回来找乡愁的地方。
回乡村找乡愁,是因为它是诗和远方。但诗和远方的前提是,我是一个已经被城市接纳的人,而不是一个归属是在乡村的人。对最终要回去的农民来讲,他找什么乡愁?乡村是他的归属,这是他的命。上一代的命,就是这一代的命,他是绝望的。他可以把房子盖得很大,但他回去以后的“业”是什么,不清楚。
所以,整个中国乡村现在的问题,核心是:让农民最后回村而不落城,这一套城市化模式带来了整个乡村支付的代价。
因此,乡村农业要素重组的革命没法发生——农业劳动力占25%,那么多人最后还得回到农村,但整个农业才占GDP的5%,那农业有什么搞头?这种结构的反常,带来农业其他的问题,机械替代了,但效率不高;我们要求化肥、农药减量,但他不用更多的化肥农药,产出就下降、回报就下来了。所以,中国农业还是一场内卷化的农业形态。
再就是村落——如果农民能够走,不回村,他可以找乡愁,但不用在原址找乡愁,而是在乡村适当的地方集聚、形成比较美丽的村落。农民在城市有着落以后,回来看到更好的景观、更好的乡村,那才是找乡愁。现在一家一个屋子,回到自己这个地方待一周就走了,那叫找什么乡愁?
他跟整个乡村的脐带在,但是乡村的状况、乡村未来的悲观和他们个人未来的归属没有希望,最后带来整个乡村的凋敝。
这是整个中国乡村问题的根结。中国城市化模式,确实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提供了这么一个制度、这套模式,但现在这些代价都出来了——在农村。
改革回村的城市化模式
乡村已经形成这种状态,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去振兴?得找到出路。光批判它没有用,光唱赞歌也没有用,光每天喊城市化再提高多少,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城市化率再高,这些人还是没有“落”。
整个中国乡村问题,是在城市化的模式上。乡村支付的这个代价,是做乡村振兴的起点。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渐进式的“落”。
城市化的问题,是人的城市化。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一定要把原来回村的城市化模式在代际开始进行改革,解决已经落城、不可能回村的这些农民的城市化,不能让70、80、90和00后继续走上一辈的老路。
70后回去不会搞农业了。如果指着这些人回去,就会变成去县城、镇上买个房,做点小生意、做点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县城和乡镇,容纳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活动吗?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回到了镇和县城,但县城、镇的凋敝跟乡村一样。原因在哪儿?它支撑不了那么大的经济活动,这些人在镇和县城经济活动的价值没有体现。
我这次回去得知,现在村里娶媳妇,不是问你在镇上和县城有没有房,而是问你在武汉有没有房。人家明白着呢:她没有觉得在县城和镇上比在村里好。
所以,首先要在人的代际上,从70后开始,把一些不回村、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市民化,真正在他的就业地、工作地市民化,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居住、社保、孩子教育,这个权利体系一定要跟城市同权。让70后往后的这些人落在他们有就业机会的地方,让他的居住、身份和他的经济机会重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慢慢就能进入正常化轨道。
很多人会说,这样的城市化,城市政府成本不就上去了吗?
城市化的成本,跟这些人在城市的贡献是匹配的。城市留下的这些人,不是闲人,不是懒人,也不是失业人口、救济人口,而全是工作人口。他们在创造财富,不是负担。
一定要在这一代开始,阻断他们回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考虑乡村的复兴问题。
村落新定义
只有当进城的人跟乡村的关系有合适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以后,乡村要素的组合、调整才变得有余地。
第一,是村落的变化。
70后的人,未来不是让他回到县城和镇,这些人应该“落”在他的就业地,乡村未来是真正成为寻找乡愁的地方。
不要去动现有的村落,这是农民的资本积累。农民过去几十年在城市挣钱盖的住房,就是他的资本。但是,在整个村落的空间结构下,可以试行按时点的存量和增量的制度调整。
比如:从70后这一拨开始,以后不再在原来的村落分配宅基地;村庄新盖房,不要在原来的村落盖,而是在乡村适度的聚居区形成新的聚落——我是这个村某个小组的,但这个小组不再给宅基地,而是在一个适度的村落聚居的地方——通过规划,比如三个小队可能形成一个村落,给他宅基地的资格权、有偿取得,进行村庄规划,形成有序、有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品的村庄聚落。老房子,如果再重新翻建,对不起,不能在原村落继续盖了,您的宅基地置换到新的村落,到那儿去盖。但不要做那种行政性的大集聚,不要发生以镇为单位的集聚——不要把人都聚在镇和县城,而是聚在适度的村庄聚落。已经市民化的人口,未来回来找乡愁,可以有偿配置宅基地。另外,村里原来已经有房的,房子用到一定年限以后,把宅基地置换到这些聚落。
这样村落聚集地适度调整后,村庄的形态,就从原来农耕的村落形态形成适度的集聚,公共服务也可以提供,乡村的养老问题也可以解决。现在老人在农村,找不到人。不仅仅是跟他在外边的儿子、儿媳妇联系不上,可能隔三五家才有一个老人,人都喊不着。但适度集聚以后,这些老人基本都在一个聚落里,在这些集聚的村落提供养老设施,老人问题也解决了。
第二,解决老人问题。
老人最主要是需要文化生活。我们村的老人,像我叔叔,每天就去村部听碟子,政府提供的这些公共品,可以用起来。现在有些地方提供的图书室,教人家怎么养殖,没用的,农民需要的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寄托。养老服务的供给,也可以政府和市场结合解决。
第三,农业问题。
当整个村落适度集聚以后,土地就更好集中了。现在地不集中,实际上是原来进城的人的地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只有把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解决,把乡村的乡愁问题解决,土地的田底权田面权分离才有可能发生。
地权的转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经营权的保障问题。经营权问题解决以后,其他的权利拓展、权利行使、抵押这些金融手段,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拥有了经营权保障的地权,再做要素的组合,才有可能发生。专业化的具有企业家性质的经营者才能进来,农业的要素组合、经营方式才能改变。
第四,村庄的公共服务。
现在村庄的公共服务,确实进步很大,但这些公共服务是在原有村落形态和村庄布局下进行的,是不经济的,有些也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而当村落变化以后,公共服务提供也变了。比如用水、文化、基础设施,不仅更经济有效,也更加为农民所需要,乡村振兴的“体面”就出来了。体面的老人,体面的村落,体面的公共服务,体面的农业,体面的人整个乡村振兴的核心,应该在这。
现在非常危险的是,都在喊产业振兴,把农业讲的不知道有多么辉煌;讲“人”的振兴,就讲人怎么弄回去;讲村庄振兴,就是怎么整村子。
为什么大量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跟现代乡村的问题到底在哪没找到有关系,跟整个乡村的需求脱节有关系,找的路不切实际。
70、80后是关键一代。解决这一代人的城市和乡村关系问题,把原来出村、回村的城市化,慢慢过渡到未来这些人落城、乡村里找乡愁;到90后、00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基本解决,乡村问题也基本解决,整个中国的城乡问题就解决了。
我这次回来以后,把我原来想的很多东西串起来了。
农村的事,最怕的就是极端
重新做乡村,也不是把现在的村落都搬掉。我们讲自然的渐进过程,新的点没有长出来,怎么自然渐进?只有阻断代际回村的城市化后,不断的有人从乡村退出,村庄才会慢慢复耕。
乡村问题的解决,不能快、不能急,但不能没办法,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没办法,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那就会变成各种指标。下面政府手上也没有几把米,还得干事,可不就是折腾农民、乱作为嘛。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拆村子、合并。要堵住这些问题,得给他路。
如果乡村振兴弄成赶人上楼、再把地腾出来给城市做建设用地指标,那没有意义的。而如果按我这个思路,这么腾出来的地,是可以城乡打通的——但不能为了建设用地指标,把人家赶上楼,而是要渐进式的。比如70、80后,就在这个村庄聚落,未来这个村庄聚落要城乡打通,成为城乡融合的区域,可以发展乡村旅游,给孩子做一些自然教育,另外也有一些人在这里居住,这些可以城乡打通。要素进到乡村,是进到这些区域,城乡就通了。这个过程,用二十年、三十年没关系,最起码,第一没有瞎折腾,第二是有路的,人不绝望。
农村的事,最怕的就是极端,危害非常之大,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极端化跟导向有关,是政府在推。任何一次政府强力在乡村推政策,不管用意多好、主观意愿多好,都会出问题。乡村经不起过强力量的主导,它是一个慢变量,也很脆弱,自身修补自己的能力很弱。
未来整个村落集聚以后,也会牵扯到治理问题。但现在一定要注意,不能把乡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混淆。很多人都试图用发展集体经济来解决乡村的产业问题,这是错误的。乡村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靠集体归堆经济来解决。
乡村治理和乡村的互助、合作,很多文化活动、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需要集体来做的。我们现在工资都给到了村干部这一级,让他们来干这个。至于搞集体经济,是另外一件事,不是你是村主任就有能力搞集体经济。搞集体经济要闯市场,要把产业搞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纽带建起来。并且,集体经济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起来的。
经济能人当村主任,也可以,但治理结构要讲清楚,公权力的行使和边界约束要解决、要清晰。不能把所有政治、经济都交给一个能人,没有任何制约,那这个人迟早也要出事。现在很多人讲,要壮大集体经济、能人治村,但不解决权力的边界和约束,最后把一批能人也治进去了,集体经济也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