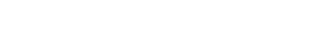关键字:
以下文章来源于搜狐智库 ,作者钟昕格
本文原题为《对话刘守英:提高农业回报率是重中之重,要保证农一代养老、农二代在城市安身》,转载自“ 搜狐智库”。转载请注明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深耕土地制度研究已有30余年。期间,刘守英教授走访中国各地,从农村到城市,不断探索土地现象背后的逻辑,并在去年获得了中国经济界最具影响力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近期,刘守英所著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增订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2019年出版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中新增了部分内容,其中专门提出了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对此,搜狐财经《致知100人》与刘守英教授展开了线下对话。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增订本)》所讨论的城乡中国是介于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中间形态,其基本特点为一半城市、一半乡村。刘守英表示,城乡中国是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的重要转变时期,不能只用城市思维看待问题,一定要有乡村思维。
“简单地提高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彻底解决乡村问题。”刘守英指出,当前中国城市化率为64%,但却出现了乡村衰败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没有带来乡村的系统性重构。
“在城市化率达到70%时,就会出现郊区化,大量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向郊区转移,就形成了城乡融合空间。”他坦言,城乡融合空间的发展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必须要保障郊区的剩余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的开发权利。
谈及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刘守英表示,当前农村存在土地破碎问题。青年人纷纷出村,农村土地留给老人耕种或者闲置,从而出现农村剩余土地的破碎和利用不足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他指出,应从整个村庄系统的土地重构来形成整片土地的利用规模化。土地破碎化和利用不足问题,涉及到农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这些土地权属一定要打通。
“乡村是一个发展空间,而不是等着被消灭的空间。”刘守英始终坚持,乡村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乡村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乡村需要有经济活动,需要有制造、服务、加工、有农业产业的延伸。
而乡村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始终面临着成本高、收益低的问题。对此,刘守英表示,提高农业回报率是重中之重,必须要提高农业报酬。首先要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最核心的就是提高要素组合的匹配度。“各个要素成本上升的背后是整个中国要素组合和配置的失衡,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要考虑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刘守英认为,一定要形成主打产业,围绕主打产业形成农业制造、农业储存、农业物流、农业加工。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农民工也面临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处境。刘守英坦言,农民的去向问题要分代际来讨论,中国农村的农民包括三代人,而当前最尴尬的就是农二代。“城乡中国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一定要保证农二代能够在城市待下来。”
最后,谈及农村发展的出路到底在哪?刘守英表示,一定要实现城乡平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拉大;其次,乡村是重要的发展空间,不能将其变成单一的要素流出空间;最后,要实现城市乡村人口互通,人一定要流动,乡村才会得到更好发展。
致知100人:在土地观上,城乡中国与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有何不同?
刘守英:
乡土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涉及到如何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实际上是人地关系。高度城市化社会的土地问题,就是土地如何来保证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的居住权实现问题。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增订本)》这本书,讨论的是这两种形态里的中间形态,即城乡中国,其最基本特点是一半城市、一半乡村。它实际上是从乡土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的重要转变时期,所以存在结构转变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第一,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土地问题;第二,涉及到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包括土地的用途转换和土地利益增值的分配问题;第三,涉及到大量体制转型,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如何推动结构转变、如何影响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
刘守英:
在城乡转型过程中,村庄发生的变化是影响转型的。城乡中国大部分空间在乡村,另外,乡村经济活动与城市高度关联,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乡村。观察中国转型的时候,不能只有城市思维,一定要有乡村思维。
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为什么在64%城市化率的时候,就出现了乡村衰败?按道理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乡村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但是中国这一轮的乡村问题,恰恰是在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候出现。
这里涉及到简单地提高城市化水平是否能解决乡村的问题。如果城市化和工业化不顾及乡村,最后肯定会产生乡村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如果考虑到如何与乡村互动,乡村本身在结构变迁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功能,那乡村就不一样了。
中国在城市化率刚过半,就出现了乡村衰败,其重要表现就是整个乡村的人口、土地、村庄和产业之间出现功能失衡。其原因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没有带来乡村的系统性重构,人口、土地、产业和村庄,这四者构成整个乡村系统。
所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往外走,但他们还得回来,整个土地关系就不能得到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无法脱离,土地制度的调整也会受到影响。产业也是一样,人地关系如果不能得到根本重构,产业还是小规模、单一的、以服务城市为主的产业,那么产业也不能得到重构。
所以整个乡村四要素之间的重构,要跟整个城乡形态的改变结合起来讨论,不能用城市化思维和乡村思维来看现在的问题。
致知100人:近郊农村应如何进行城市化?
刘守英:近郊问题还是城乡之间形态的重构问题。近郊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和发达地区的乡村,这些通通把它归结为城乡融合的重要区域。
在城市化率到70%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郊区化,大量城市人口往郊区居住,因为城市存在拥挤、烦躁、交通、治安等问题;同时,从乡村进来的很多人,也都落到近郊、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地区,这些地方是城和乡之间重要的结合空间。所谓郊区化,就是人口、产业、生活设施,公共投资等开始往郊区转移,这些地方就形成了城乡融合空间,中国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
目前城乡融合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不往这里投,结果就是本地人在这投,大量的地被征走,本地人留一部分的土地,在这里自己盖房、自己出租,形成一个非正式空间。
这些空间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就是这些地方剩余的土地,是否平等享有跟城市国有土地一样的开发权利。因为整个农地转非农用地都一律实行征收,这些地方如果继续只用征收的办法,农民就分享不到增值收益,最后就开始自己盖房、违规使用,为了获得增值收益。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平权,要让这些土地平等参与到城市经济活动、非农建设中。所以核心是土地,如果不让这些地方的土地参与非农经济活动,土地就继续被征收、继续被做房地产,结果就形成城市和农村两张皮,中间夹了非正式的发展空间,而形成不了城乡融合空间。
致知100人:如何看待乡村产业的单一化?如何丰富乡村经济活动?
刘守英:
如果在纯城市化思维下,乡村是必然会单一、必然要衰败的。整个乡村产业的单一化,实际上是这种单级城市化社会的结果,把人转向城市,乡村就是提供食物、提供粮食,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就是乡村产业越来越单一、乡村产业越来越没有回报、从事乡村产业的人越来越老人化。
所以乡村本身的功能,在整个城乡融合阶段,就不能只是提供粮食、提供劳动力输出的空间,乡村空间是一个发展空间,而不是等着被消灭的空间。乡村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说乡村的整个经济活动要恢复复杂性,不能是单一的。
城乡融合以后,乡村也需要有经济活动,有制造、服务、加工、有整个农业产业的延伸,乡村需要有非常多样化复杂的经济活动。粮食对农业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重点是做粮食产业的这些区域,一定要做成强大的粮食产业。
比如一个县不能搞很多产业,做一到两个产业,比如粮食为主的产业县,就围绕粮食产业实现工业化,整个农业种植规模围绕粮食展开。
同时,其加工、物流、农业服务都围绕一个产业,这样就形成一个规模化产业,这样可以提高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乡村现在不是没有路,乡村的路要在新的思维上来推动。
致知100人:农业成本高但回报率低,如何提升农民收益率?
刘守英:
必须要提高农业报酬,如何提高农业回报率是重中之重。提高农业的回报率,第一,要把成本降下来,没有回报的核心就是所有成本居高不下。
第二,劳动力成本高、农村发展其他产业的机会成本上升、劳动成本高、地租高,机械成本上升。所以要降低这些成本,最核心的是要提高要素组合的匹配度。
农业工业化的核心就是要素之间如何进行更好组合,就是土地、资本、劳动、服务要进行有效组合,来降低现在单要素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上升。
为什么没有进行有效的要素组合?与城市化、工业化模式相关。大量的人出去还得回来,人地关系就不能调整,人和地就没有有效匹配,土地就实现不了适度规模,因此,越扩大规模,成本就越高。所以各个要素成本上升的背后是整个中国要素组合和配置的失衡,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农业要提高回报,就要考虑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一定要根据中国土地资源稀缺的特点,在如何提高单位土地报酬上想办法。另外,每个县的农业一定不是要发展很多种的产业,一定要形成主打产业,围绕主打产业形成农业制造、农业储存、农业物流、农业加工。
刘守英:
在农村里存在土地的破碎问题。土地破碎问题的表现是一家一户,基本上年轻人出去,土地都给老人种、租给别人种或者就空着,这就是土地破碎和利用不足。
现在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是破碎化、利用不足,但现在规模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应该从整个村庄系统的土地重构来形成整片土地的利用规模化。这些土地破碎化和利用不足问题,需要国家政策来解决。因为涉及到农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这些土地的权属一定要打通。这些权属不打通,土地就没有办法整合利用,就很难形成规模化的土地使用,一定要考虑清楚,如何让本来非常稀缺的土地进行整合、规模化。
致知100人:1997年我国实行了第二轮农民土地承包,年限为30年,2027年将实行第三次土地承包分配,您认为接下来是否会对耕种面积进行重新分配?
刘守英:
上一个承包期到期以后,接下来原有农民的承包权是不是要得到承认?这个不要怀疑,已经宣布了,30年过期以后再续30年,就是为了保证承包权问题。
承包权的稳定,稳的就是原来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成员的权利,只有成员才能获得承包权,这个权利30年到期也不能改。但是并不等于拥有承包权,土地就一直在你手上。三权分置的作用就是每一个成员的承包权是原来成员拥有,在承包权保证的情况下,一定要把经营权做成独立权利。
经营权流转以后形成的经营权,因为大量的人现在都出村了,所以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抵押权,这些权利要真正落实。落实以后,未来进入农村的经营主体,就能很好地把土地经营起来。
这里面有两个重点:首先,承包权是原来集体组织成员的,不能动摇。其次,未来经营权要真正做成独立权利,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所以未来一定要保障承包权,同时把经营权做成独立权利,这样经营者才能更好地利用土地。
致知100人: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主体是谁,分配机制是什么?承包权、所有权、经营权,哪个应该优先?
刘守英:
农民的承包权不能去掉。原有的集体组织成员对承包土地的承包权不能丧失,意味着这个承包权,第一,有收益权,土地转租出去,转给企业、大户,地租不是集体的,是农户的地租。
第二,你用我的土地去发展旅游、做产业开发等,农民不是只吃一个地租,农民承包权要和经营权谈判,就是地租。城市的地租收益会不断上涨,农村也应该有相应的上涨机制。
第三个,农民的土地包给第三方,第三方不好好利用,或者把土地耕作层破坏了,又或者没有按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去使用,最后导致土地破坏,农民是有权利收回的。所以要在权利的实施上,有更完整的实施规则,这样既保护农民承包权,也保护种地的经营者的经营权。
刘守英:
中国城市化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土地抵押融资,实际上现在不允许用土地抵押融资了。允许地方政府发专项债,但是不允许利用土地抵押,现在到了思考整个土地抵押融资功能的时候了。
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还在大幅增长,原因就是城市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开始靠债务。原来有土地抵押时的好处就是说地方政府拿着土地抵押就能从银行拿到钱,然后靠土地抵押去获得融资资金。
但后来为什么叫停?因为做过了。土地抵押的评估和土地的未来预期收益,在整个制度环节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地方政府只要征来土地,把它放在平台公司一评估,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这就产生了土地抵押的融资风险。叫停土地抵押是因为原来的土地抵押制度不完善。
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融资实际上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升值以后,作为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城市化过程中主要升值的是土地,城市建设的结果是土地升值。土地升值以后,一部分用来做城市建设,这个链条是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完善制度还是一刀切?我们把它一刀切断以后,最后债务还在不断增长。所以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发挥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升值对支撑城市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盲目用土地抵押,超额获得银行资金。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发展能力,土地升值空间也有所不同。所以就需要有更完善的土地融资制度来支撑城市建设。
致知100人:如何解决农民工“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处境?
刘守英:
农民的去向问题要分代际来讨论,整个中国农村的农民实际上是三代人,40、50、60、70,基本上是农一代,他们对土地有感情,也发展过农业,这些人肯定是要回乡村的。
第二波就是农二代,80后、90后。他们没发展过农业,但他们知道自己是农民身份。这些人现在是不愿意回村,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城市化了。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这一波人,他们不想回村,也回不去村。
第三波就是农三代,主要是00后,他们基本上是在城市出生,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所以现在城乡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三代人怎么摆布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农一代,应该让他们在乡村有体面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基本养老保障,乡村的养老设施等。
农二代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不愿回村了,不能让他们被迫再回到村庄。城乡中国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一定要保证农二代能够在城市待下来。在就业和工作的地方,就地城市化,而不是回到乡村。
农三代完全跟农村没有瓜葛了,所以这些人一定要有公平的教育、公平的居住权、公平的就业权。
农一代体面地在乡村老去,农二代过渡到城市,农三代彻底城市化,整个中国的人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这里面的核心是基本权利的问题。农一代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要保证,包括养老、文化;农二代入城的权利要保证,包括就业、居住等基本权利;农三代市民化的基本权利要保证,包括居住、教育、公共服务等,这样就能顺畅地从城乡中国转型到城市中国。
致知100人:农民融入城市后,其宅基地房子的产权该怎么办?
刘守英:
农一代基本还在农村,土地不是问题。农二代应该是整个城市化中非常重要的人群,他们进入城市以后,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的资格权、集体建设用地的分配权还是他们的。
但并不是说,承包地还是他们在种、宅基地还是他们在住、建设用地还是他们在用。这些人基本上两权分离了,他们通过持有基本权利,有一定收益,但是土地使用转给其他人,这里也包括本村和外村的人。到农三代就彻底城市化了,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刘守英:
接下来就是城乡如何打通的问题,城乡要素要能够实现对流。未来乡村应该具备两种独特优势。第一,乡村人口进一步城市化,土地重新整合,产业不断专业化、复杂化,这时的村庄就可以适度调整,未来的乡村应该是中国乡村文明延续的地方。
另外,大量的人进入城市,整个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基本在城市,但是乡村的根是要留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乡村未来就是一个农民养老的地方。
这些出去的人,回来寻找的是诗、远方。他们每年还是会回来,家园的半径适度扩大,农民对乡村的住房、文化设施、公共空间进行适度改造,乡村就可以建得很漂亮。这样城市中一些对农村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也愿意留在乡村、愿意对农村进行投资,这时城乡就打通了,乡村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变化以后,就有一些城里的人进到乡村来,出去的农民每年也会回到乡村,那么乡村就活起来了。村庄的文化活动建设、公共设施投资、土地整理、产业发展就进入乡村,乡村整个空间就会成为一个发展空间。
致知100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
刘守英: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讲,农村发展的出路,首先一定要平衡发展,不能只有单级发展。如果只有城市发展,乡村一定会衰败,所以城乡一定要平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拉大;第二,乡村一定是重要的发展空间,不能把它变成是单一的要素流出空间,这里一定要有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第三,人一定要流动,会有农村的人出去,也会有城里的人进来,这样乡村就会得到更好地发展。